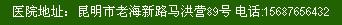|
20世纪遍布暴力与幻灭,压迫与独裁,是一段最好忘却的阴暗历史;但有人却想再次丈量它。这就是《思虑20世纪》一书要做的事。 《思虑20世纪》是托尼·朱特、蒂西莫·斯奈德两位历史学家的对谈,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朱特在病榻完成的生平回顾,也是朱特最后一次沉思他生活过的这个世界。在对20世纪最好的智识生活的恢复和示范中,《思虑20世纪》敞开了一条通往21世纪道德生活的道路。这是一部关于过去之书,但也是关于我们应为之努力的未来的一份申辩。 《思虑20世纪》于年出版,这一年“渐冻症”终于卷走了朱特的生命。它成为了朱特的临终绝唱,成为他对20世纪历史真相、智识生活的最后陈词。今天,阿信将本书中的跋节选给大家,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位历史大家对于20世纪的思索。 托尼·朱特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年,以其“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跋 文 托尼?朱特 当蒂姆?斯奈德在年12月第一次找到我,提出一系列对话题目时,我还抱有些疑虑。在这3个月之前,我被确诊患上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我对自己未来的计划殊无把握。我本打算开始写一本新书:一部关于20世纪社会思想的智识史和文化史,这本书我已经考虑多年了。但该研究所牵涉到的—更不用说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已不再是我能够驾驭的了。这本书本身我已经打好了腹稿,而且很大一部分都已做了笔记,但我是否能完成则尚未可知。 年,托尼·朱特被确诊患上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此外,这样一种持续性交流的概念也不是我所熟悉的。和大多数公共作家一样,我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但几乎都是关于我已出版的某本书,或者是某个公共议题。斯奈德教授的提议则很不一样。他所建议的是一个漫长的系列访谈,它们会被录音并最终整理成文,这些访谈将涵盖多年来主导我的研究的多个主题—包括我构想中的那本书的主旨。 我们就这一想法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我被说服了。首先,我的神经系统疾病是好不了了,如果我想继续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进行工作,我需要学会“谈论”自己的想法: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对头脑没什么影响,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所以人还是可以自由思考的。不过四肢瘫痪了:写作最多也成了一项二手活动,即口授。这极有效率,但确实需要一些适应。作为过渡,录音访谈似乎是一个相当实用甚至是很有想象力的办法。 …… 如果我想要“谈论”20世纪,显然需要一个人,他不仅有能力就我自身的专业领域进行提问,还能够将相应的我自己只是间接了解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带进对话中来。我对中东欧做过颇为详尽的论述,但除了捷克语(和德语),我不敢称自己对该地区的语言有任何了解;我也没在那里做过第一手研究,尽管往来频繁。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最初限于法国,后来才扩展至西欧大部和政治观念史。斯奈德教授与我因此是理想的互补。 我们共有的不仅是对历史的兴趣,还有对政治的关切。尽管存在着代际上的差异,但我们都怀着类似的不安经历了后的“蝗虫年代”(locustyears):最初是乐观主义和对“天鹅绒革命”的希望,然后是克林顿时代令人沮丧的自命不凡,最后是布什—布莱尔时期的灾难性政策和做法。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上,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这几十年在我们看来是被挥霍掉的:在年,尽管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激起了一些乐观情绪,但我们对未来都忧心忡忡。 …… 那么,20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够对之说些什么—或如据传的周恩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妙评,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不能迟迟不做回应,因为20世纪被贴标签、阐释、援引和抨击要多于任何一个世纪。新近关于它的最知名论述—著者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短暂的20世纪”(从年的俄国革命到年的苏联解体)形容为一个“极端的年代”。这一关于20世纪诸多事件的颇为阴郁—或至少发人深省—的解释回荡在许多年轻历史学家的作品当中:马克?马佐尔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将其关于欧洲20世纪的论著取名为“黑暗大陆”。 但如果我们不以一段恐怖叙事作为开始,那会如何?事后看来,且仅仅事后看来,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一般境况的显著改善。医学发现、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比年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更长,也更健康。他们也更为—从我刚写的那部分内容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怪异—安全,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 这或许可被视为这一时代的某种矛盾性:在许多业已成立的国家里,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但由于国家间冲突的空前高涨,与战争和占领相关的风险也急剧增强。因此从一个视角来看,20世纪只不过延续了19世纪所引以为豪的进步与发展。而从另一个视角看来,这是向17世纪—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年)让国际体系稳定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前—国际无政府主义和暴力的令人沮丧的回归。 托尼?朱特已出书目:《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责任的重负》《论欧洲》等 事件呈现在当时人面前时的意义,与我们今天看待它们的方式似乎有极大的不同。这可能听起来很明显,但实际则不然。俄国革命和之后共产主义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铸就了一种强有力的必然性叙事;在这一叙事里,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不管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是某个未经明确指明的时刻。即便是那些对这一前景感到绝望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也绝非没有可能,并且其影响塑造了这个时代。 这是我们很容易便能理解的—年尚未遥远到我们已然忘记,共产主义的前景对那么多人来说曾是如此可信(至少在他们经历过之前是如此)。我们已经完全忘却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最有望替代共产主义的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而是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意大利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强调了威权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公开抛弃(直至年)了纳粹版本的种族主义。到“二战”爆发时,认为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选择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自法西斯主义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之后—的人,比我们今天所愿意承认的数量要多得多。 由于这两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如今都已经(在制度上,如果不是在智识上的话)烟消云散了,我们很难回想起某个时刻;在那时,跟为它们所共同鄙视的宪政民主比起来,它们更有望获得成功。而这样的文字则无迹可寻,即宪政民主会赢得人心,更不用说赢得战争了。 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20世纪被暴力的威胁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给主宰了,但除非我们明白这些极端主义吸引了比我们所乐意承认的多得多的人,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20世纪。自由主义最终取得胜利—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各个不同制度基础上的重建—是真正意料之外的时代发展之一。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证明了它惊人的适应能力:其何以如此,正是本书的主旨之一。 托尼?朱特的卡通形象 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亲身经历过人们所叙述的这些事件似乎是有好处的。时间的流逝造成了许多障碍:物证可能不足,我们主人公的世界观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而习以为常的范畴(“中世纪”“黑暗时代”“启蒙”)给人们的误导可能比解释更多。距离也会成为一种障碍:对语言和文化缺乏了解,即便最勤奋者,也会被引入歧途。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或许对一种文化的理解比当地人更为深入,但他们也并非永不犯错。 然而,熟悉也有自己的困境。历史学家可能会让传记性的洞见影响其冷静的分析。我们被教导说,学者应与其作品保持距离,而且大体上这是审慎的建议—看看当历史学家变得比历史更为重要(至少在他自己眼里如此)时会有何后果。但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带着我们自身一生中的偏见和记忆,而且有时候这些偏见和记忆会派上一些用场。 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年,是我近年来一直撰写的这段历史名副其实的同代人。我至少亲身观察到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这不能确保拥有一个客观的视角,甚或更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于提供某种鲜活感。在场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这是不带感情的学者所缺少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为是”(opinionated)时所指的意思。 托尼·朱特逝世前,在其纽约家中这又有何妨?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历史学家(或事实上任何人)不会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论述自身时代的著作中对人和主导性观念没有主观的看法,这也着实怪异。一本自以为是的著作与一本为作者偏见所扭曲的著作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是:前者承认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质,且并不佯称绝对的客观。就我自己来说,无论在《战后欧洲史》还是在更晚近的回忆性文章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视角立基于我所出生的时代和环境:我的教育、家庭、阶级和世代。这些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解释,更不是对与众不同的阐释的一种辩护;它们只是给读者提供一种对它们进行评判和情境化的手段。 …… 我若是没有写过十几本著作和数百篇特立独行的文章,可能还会担心,这些对话和反思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唯我论。我还没写过自传,尽管最近几个月里我发表了回忆录的一些梗概,而且我仍然十分确信,对历史学家来说,恰当的默认模式便是修辞上的隐身。不过在得到鼓励而透露了我个人的些许过往之后,我承认这对理解我个人在关于其他过往的研究上的贡献很有帮助。希望其他人也有同感。 年7月5日,纽约 本文摘编自《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 [美]托尼·朱特[美]蒂莫西·斯奈德著 年3月 点击“阅读原文”,北京白癜风治疗中心白癜风哪个医院治疗得好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干细胞治疗疾病如此厉害,所以有万用细胞
- 下一篇文章: 1825岁的你,就是一个渣